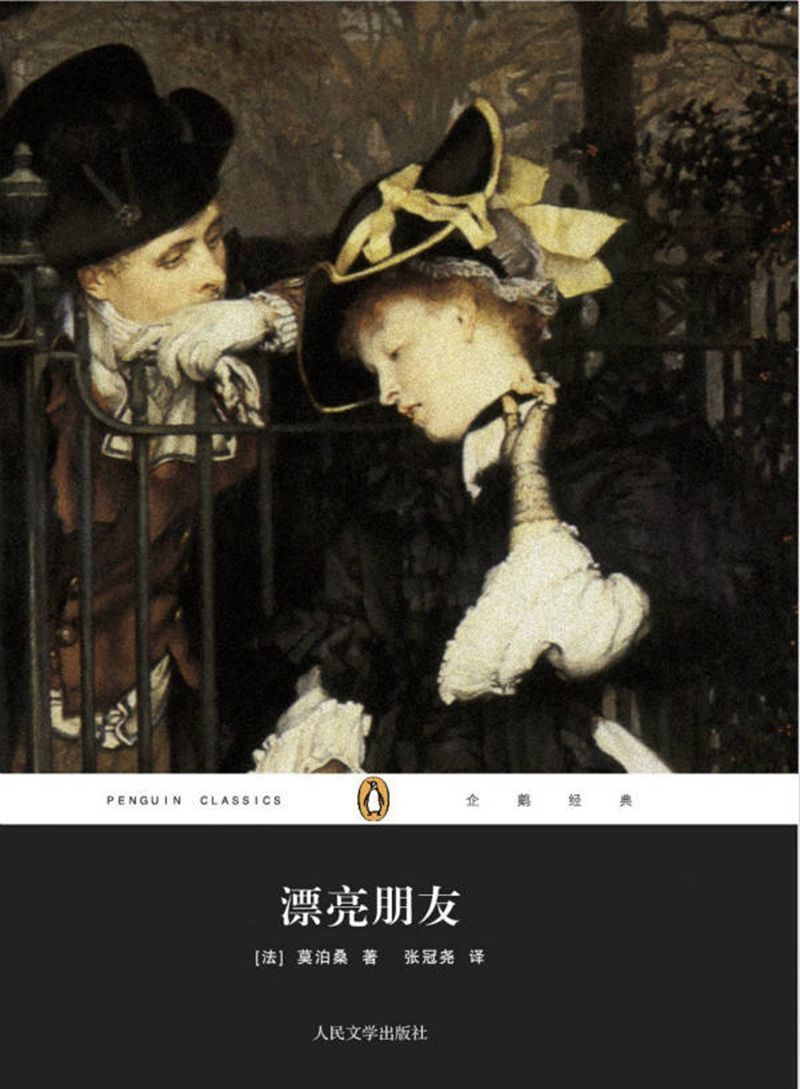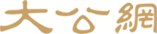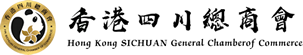【亞洲文旅網訊】作於青年時代的《欲望》一詩,在某種程度上便是莫泊桑一生的寫照。他將自己塑造成拉丁文藝界的典型,崇高、放縱,而這個文藝界也在他逝世後於一次次危機中瓦解。托爾斯泰對此做了蓋棺論定,“在培育莫泊桑成長的那個圈子,對女性的美和愛情的描寫是十分嚴肅的,這種描寫也早已被那些淵博的智者和學者所確認和承認,並且曾經被認為,現在也仍然被認為是最崇高的藝術的真正任務”。這位道德色彩極為濃重的北方基督教徒將鋒利的矛頭對準了歐洲十九世紀後半葉最風流的作家,他指責莫泊桑“對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利益不了解,把他們看成僅受情欲、惡欲和私利所驅使的半人半畜的東西”。
的確,莫泊桑筆下的人民並不是以東正教、無政府主義、早期社會主義的面目出現的。以二十一世紀的眼光看,他的人民也顯得老套、過時。不過,莫泊桑和他的同時代作家們共同開啟了現代短篇小說,某種程度上它和高效的、流程式的世界工業體系,和現代公民社會的形成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與莎士比亞或塞萬提斯的文學盛世不同,莫泊桑生活的年代可以說是文學最為輝煌的時代,它居於由思想體系、政治方略、工業體系、媒介革命構成的世界圖景的中心位置。而莫泊桑或許是迄今為止最為流行的短篇小說家,這得益於他的語言的簡潔或者更強的可譯性,他對人物和故事的聚焦,他對情欲和失落的野蠻的追求。當然,這也使得他無法見容於現代學術體系,尤其是文學史和文本分析的那種。
7歲時的莫泊桑
1850年8月5日,居易·德·莫泊桑生於法國諾曼第濱海塞納省都爾絮阿格鎮的米龍梅斯尼爾別墅。父親是紈絝子弟,尋花幽歡的慣犯。母親是作家勒普瓦特萬的妹妹,福樓拜的朋友。父親和母親在婚後常常爭吵,最終協議分居,沒有在法律上離婚,但幾乎是事實離婚。莫泊桑交由母親洛拉監護。對於父親,莫泊桑沒有過怨言。9歲時讀拿破崙王家中學的居易有一次寫信給母親,“我作文得第一名。作為獎賞,某夫人帶著我和爸爸上馬戲團,她好像也要獎勵爸爸,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1862年,由福樓拜簽名的《薩朗波》郵寄到埃特爾達鎮的一棟別墅。洛拉給兒子居易朗讀了若干片段,隨後她致信福樓拜,“我兒子居易聚精會神地聽著,你的精彩動人、細膩和恐怖的描寫,使他眼神閃出光芒。”就這樣,少年的居易一邊在母親朗誦的莎士比亞中,一邊在海濱衝浪嬉戲中,逐漸長大,肉體的和文學的這兩股力量主宰著他的一生。在他的體內流著“海盜的血”,也流著赫耳墨斯的血。
像大多數作家一樣,莫泊桑對教會學校、拉丁文、祈禱表示厭惡,他熱愛漁船、舞會、愛情。少年的居易在《新愛洛伊斯》等作品的啟迪下開始寫詩,“生活是遠去的船隻的痕跡,也像長在山上瞬息即逝的花朵。”1868年,居易救起詩人斯溫伯恩,這位前拉斐爾派詩人給居易留下了古怪、哥特式的印象:死人頭、被性虐的猴子,還有他的性錯亂。這不是詩人第一次和詩歌世界擦身而過,他曾被母親洛拉介紹給她的朋友、詩人路易·布耶,不過詩人不久撒手人寰。“如果布耶活著,他會使居易成為詩人。”母親說。
福樓拜教導居易要有耐心,“……按照布豐(布封)的說法,才能不過是長期的忍耐……”,要尋找合適的、準確的詞,“……當你經過坐在門口的雜貨店老闆、或正在抽煙的看門人……你給我指出這個老闆或看門人的姿勢,他們的包括整個思想本質的、由形象的動作指明的外表形狀,使我能夠不與其他雜貨店或其他看門人搞混,用一個詞來表明……”。這種對於準確,對於創造的要求在很大意義上並非現實主義或者自然主義的部分,而是藝術家品質的部分。尋找和描述事物的本然面目可以看作是那些大師或藝術家們和現實主義合作的結果,正如加繆所言“藝術從來不是現實主義的,它往往有著達到現實主義的願望。”
1870年,取得文學業士後,在巴黎法律學院註冊不到一年時間,居易參軍了。從1870年7月,到1871年11月,居易一共在軍隊待了一年餘日。從軍的日子裏,居易隨軍一直潰散,十分狼狽。給母親的信中,他寫道,“普魯士人在我們的國土上急速前進。至於戰爭的結局那是毫無疑義的。”他也曾盲目地相信可以守住巴黎,但事與願違。居易覺得被德國擊敗的法國就像是被擊倒的、顫巍巍的拳擊手。沒有證據表明,後來的莫泊桑對於戰爭有著宏觀的認知,他甚至都不清楚巴黎公社究竟是怎麼回事。
在後來的作品裏,莫泊桑對於戰爭的描寫有著諸多虛化的和模棱兩可的一面。像我們對於現實主義的既有認知那樣,這些作品裏對於戰爭場面幾乎是一筆帶過,且多數還是象徵的和描述的手法。他的小說熱衷於描寫士兵、將軍、人民、伯爵夫人,而不是成百上千個他們;熱衷於描寫他們的日常、道德、心理,而非事件的機理、事態的流變,甚至是故事的開合。在這些作品裏,莫泊桑所講的仍然是喜劇性的道德故事,他從未真正地將戰爭或者政治納入作品的核心。

《羊脂球》
在普法戰爭紀實錄《羊脂球》裏,莫泊桑看起來很輕巧、很因襲地寫了幾個典型:不可撼動的自然、破敗無力的法軍、野蠻傲慢的普魯士、善於隱藏和變化的伯爵和太太、假信仰之名的修女、性欲旺盛的男人、死氣沉沉且壓抑人心的道德、無辜的奉獻的人,但他們又的的確確是那個世界的幾個主要形象。像在其他短篇小說中一樣,莫泊桑給我們一個滑行般的開場,而後是一個可以預見結局的故事,接著是果然到場的轉折,最後是猝然而至、猶有餘韻的結尾。羊脂球無疑是一個耀眼的主角,她是拿破崙三世的崇拜者,戰亂中的流亡者,為救一行人不得不委身於敵人的良心人,被遺棄的可憐人。圍繞“妓女”“救星”“棄女”,她不再是確定的那個主體,她時而像塞壬,時而像彌賽亞,但終究不是她自己。小說裏說,“她感到這幫道貌岸然的人先是犧牲掉她,然後又把她當成沒用的髒東西扔掉,現在又將她淹沒在鄙夷不屑中。”這裏所說的何曾不是讀者看到的“羊脂球”呢?
莫泊桑好多次將普法戰爭安置在自己的故鄉諾曼第。為給自己的父親和兒子復仇,米隆老爹“像割麥穗似的割下”十六個敵人的頭。在不斷的回轉和不得已的逃亡後,瓦爾特·施那夫斯如願以償地做了俘虜,如願以償地獲救,淪為上校獲取勳章的籌碼。相比之下,他對戰期巴黎的書寫要寥落一些。在戰前常聚在一起釣魚的瓦勒良和莫裏梭感:歎“……日子可比以前艱難……倒楣的世道……”他們被普魯士們縛石投河,“現在輪到魚來吃他們了。”當然,寫戰爭的還有《菲菲小姐》和未完成的《天使》。
1873年,莫泊桑入職海軍部(此前自願服務約一年),1878年轉入教育部,1881年離職。莫泊桑對於職員生活多有苛責,他志不在此,他抱歉自己的存款不夠海邊度假。後世認為莫泊桑是他曾經所是的小資產階級的最佳寫手,或許就是這樣。他幾乎將人文系統中的舊的道德騙術改造成新的道德可能,他壓平場景、聚焦人物、減弱高潮。
與此相對照的是莫泊桑對待性、愛情、婚姻的風流和恣意,他渴望長出千只手擁抱女人們,有時於他而言,“女人只能是取悅男人”。他在入行前就習慣於去妓院,並早早染上了梅毒,甚至成立了一個曖昧的組織“克雷皮蒂斯社”。在信的那一頭,福樓拜苦口婆心地叮囑,“……工作上要更用心……你是為寫詩而生,多寫點東西吧!其他都是白費精力,不要貪圖肉體享樂,要注意健康!……從早晨5時到10時,這些時間要貢獻給詩神繆斯……作為藝術家,只有一個原則:一切要貢獻給藝術。……”但對於生活問題,莫泊桑只是一個表演者,福樓拜只是一個觀眾。1875年,莫泊桑自導自演了一出情色劇《玫瑰之葉》,它的主角是乳房和生殖器。福樓拜、屠格涅夫、左拉都做過一次觀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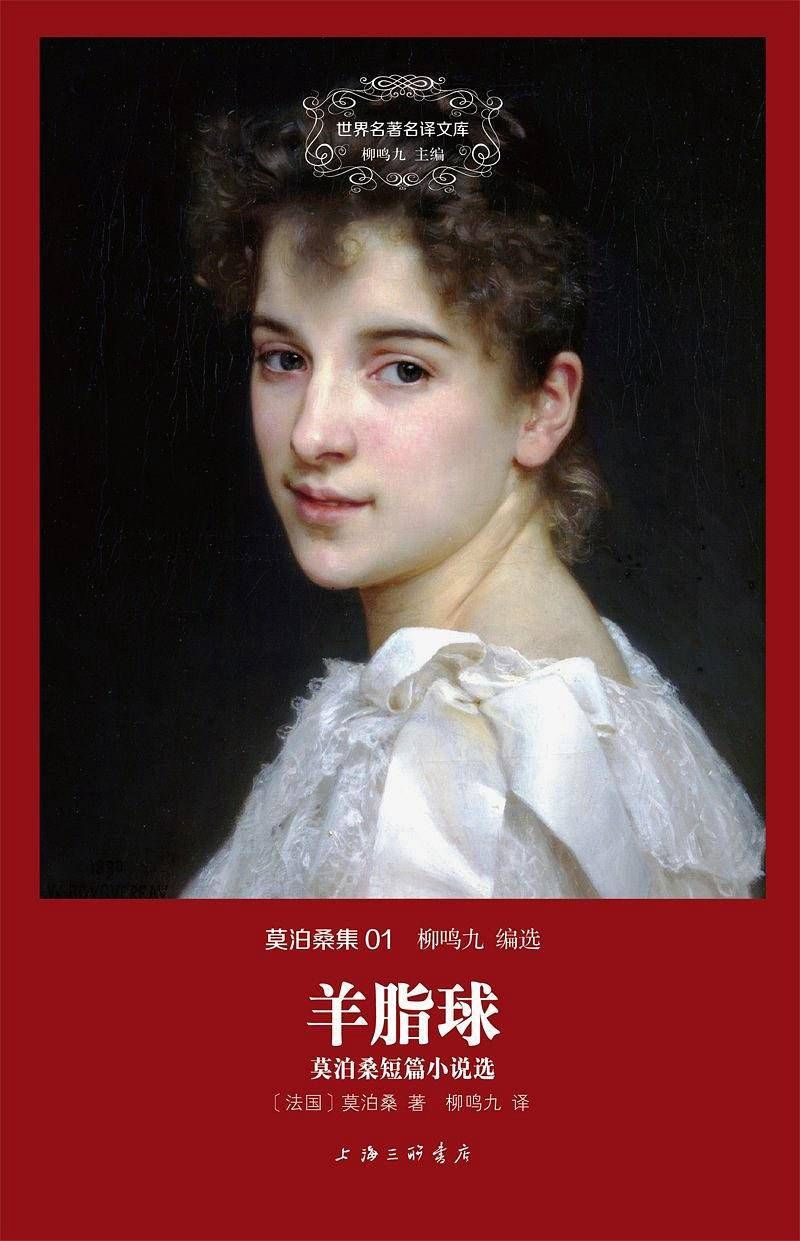
莫泊桑
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世界是新興大眾媒體的,是一毛錢小說的世界。大量的報紙囤積了大量的撰稿人隊伍,而作家們,尤其是現實主義作家們或多或少處於該隊伍的中心。關於“現實主義”,最早見於尚夫勒利與杜朗蒂的筆下,他們主張“對人們的生活環境進行確切、完整、真實的再現,因為這種研究方向得到了理性、智力的需求及公眾興趣的證實,並且沒有謊言或任何弄虛作假的行為”。這是彼時的未來世界。
當然還有一部分作家維繫著古老的沙龍方案。馬拉美將自己的家改造成文學客廳,做起了“星期二聚會”,與會者包括馬奈、裏爾克、紀德、瓦雷裏、德彪西。而莫泊桑和一部分自然主義者走的是更具有“現代性”的路線,他們也大抵收穫了更多的文學聲譽和財富價值,只不過他們的文學趣味和文學史地位一直都是受到指摘的。莫泊桑溜進媒體的另一個原因是他不想歸屬於任何教條、學派、女人,這些媒體滿足了他對於獨立的需求。他和自然主義者們保持著有距離的合作關係,他們在1880年出版了合集《梅塘之夜》。他和《文學界》《高盧人報》《吉爾·布拉斯》等媒體建立了長時間的合作關係,或發評論,或發隨筆,或發小說。
經過十年的蟄伏和忍耐,莫泊桑終於收穫了女人、金錢、聲譽。在十九世紀末,莫泊桑就是現實主義文學的高潮。對出版商和金錢的要求,他是毫不手軟的,“……一本書10至15篇小說,連插圖共150頁,精裝版500冊,共2000法郎。在我交稿時付1000法郎,在發售時付1000法郎。……”經由屠格涅夫推薦,莫泊桑的作品在俄國也流行起來,甚至贏得托爾斯泰的關注——托爾斯泰指責莫泊桑的大多數作品沒有良好的道德感,但他毫不懷疑作家的才華和探索。莫泊桑的收入被他用來買別墅如“居易之家”、遊船如“俊友”和贍養家人。他既不想建築一個更好的人文世界,像龔古爾那樣,也不想踏入老舊的文學作坊,像雨果那樣。
《俊友》(《漂亮朋友》)幾乎是莫泊桑的自傳,杜·瓦洛就是莫泊桑,莫泊桑就是杜·瓦洛。杜·瓦洛道貌岸然,憑藉自己的姿色和手段,坐上了《法蘭西生活報》主編,並贏取了瓦爾特的女兒。他成功得一塌糊塗,連主教都祝福他,“您肩負重任,必須做出表率。”在婚禮中,他感受到由衷的幸福感,渾身戰慄。莫泊桑聲稱,他記錄下的道德現狀正是現實。為此,讓我援引托爾斯泰的觀點,他認為莫泊桑打心眼裏覺得這個社會是“敗壞的、瘋狂的、恐怖的”,這歸根結底是因為莫泊桑相信人的靈魂有著另外的要求,尤其是在愛情問題上。當然,讀者且不要將特定現實造成的中產階級化的社會事實和此類褊狹道德的風行做統一觀。莫泊桑的辯解仍然是有效的,尤其是當我們見證俊友的瀟灑、情欲、隱晦的時候,當我們見證這位披掛著聲望的作家日漸凋零的窘境的時候。

《漂亮朋友》
沒有證據證明莫泊桑準確地傳遞了他的或者他時代的文學價值取向。在他的隨筆式論文《小說》中,他將自己定義為“客觀小說的理論”的追隨者,以區別於“純粹分析小說的理論”的信徒。但是他的解釋頗為混亂,尤其是他沒有對自己下的斷語做出有效的界定。他所說的“分析小說”像傳統的道德小說,又像當時的通俗文學,又像未來的心理小說。從今日的角度來講,莫泊桑正處在叔本華的意志哲學和現代心理學的中間,他的作品也仍然是兩者之間的。他可以聲稱自己的作品是“具體形體的純樸性”的,是“從他深刻慎重的觀察中綜合得出來的方式審視宇宙、萬物、事件和人”的,但它又必須是心理學的,或者行為心理學、“故事”心理學的,而這正是他被二十世紀短篇小說大師們追捧的最重要原因。
正如他在《狂人日記》中所寫,他也在精神錯亂,掌控不了腦袋,同時他完全學不到他命名屠格涅夫的那種東西——虛無主義。在後期,他越來越背離福樓拜的傳統,“作品不再是作為作品造物主的作品的自身反映”。在僅有的一些時刻,莫泊桑對自己的生命是友好的,主要是乘“俊友”旅行的時候。1888年,他記錄了自己在地中海的行跡,“……我們需要全神貫注,準備戰鬥:眼睛需要善觀天色,發現捉摸不定的外表上的變化;皮膚需要感覺靈敏,分辨它是在撫摩還是在衝撞;心靈需要摸透它的脾氣,料到它什麼時候發作,判斷它是心平氣和還是恣意任性。……”他在海洋和乙醚之間尋找到了難得的平衡。
1893年7月6日,在梅毒、過勞、精神問題等的持續惡化下,莫泊桑在一家精神醫院離開了人世。關於他的生活,我們所知甚少,因為“有關他的私生活,他對我們諱莫如深”。在他的葬禮上,左拉致辭,“那些不認識他的人將通過作品都愛他,因為他歌唱了永恆的愛,歌唱了人生。”